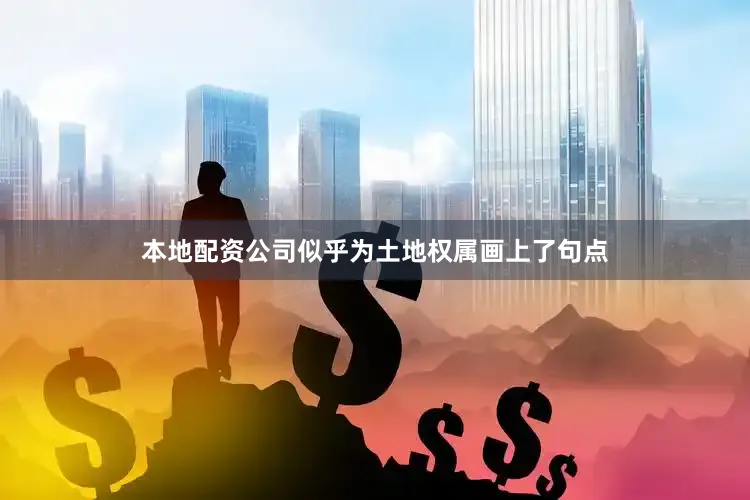
在辽东大地上,抚顺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藏着一段关于 "新抚顺" 的往事。从日俄战争时期的资源争夺,到伪满时期的仓促迁徙,再到上世纪末的棚改浪潮,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都刻着时代更迭的印记。
从千金寨到新抚顺:一段被煤尘覆盖的历史
抚顺的故事,绕不开 "煤"。明朝时设仟金所,1904 年日俄战争后,这里成了列强争夺煤炭资源的战场 —— 战前帝俄强占采煤,战后又被日本霸占。随着人口聚集,1908 年此地改称千金寨,1915 年抚顺县治迁此后渐成政治中心。彼时的千金寨,南抵千台山麓,北接大官屯,东西横跨五里,南北纵贯四里,七八万人口在此生息。
但地下的厚煤层,成了此地命运的转折点。日人觊觎煤层,想以 "大揭盖" 式露天开采,1927 年前多次与中国当局磋商未果,便用 "只采煤不填充" 的手段造成地面沉陷。直到伪满时期的 1936-1937 年,千金寨居民被迁往沈抚铁路北侧、浑河南岸 —— 一片用废矸石垫起的土地,日本人称之为 "新抚顺"。仓促间的迁徙,让这里成了大片棚户区,简陋的房屋在岁月中风雨飘摇。
上世纪最后十年,新抚顺的命运迎来转机。市政府启动棚户区分期改造,试图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然而,改造的齿轮转动时,却卷入了一场延续多年的争议。
展开剩余71%棚改浪潮中的博弈:从拆迁协议到权属迷局
1995 年,抚顺市兴顺房屋开发公司中标新抚顺棚厦区改造二期工程二十五方块。按规划,9 号楼需拆迁抚顺市燃料总公司和市政设施管理处的房屋与土地。兴顺公司很快与燃料总公司达成回迁安置协议,但与市政管理处的僵局,让 9 号楼规划最终取消。
四年后,抚顺市日新公司接过接力棒。1999 年,日新公司与市政设施管理处以房屋置换达成拆迁协议,兴顺公司也将燃料公司的住宅及土地作价 100 万元转让给日新公司。两公司的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均交由日新公司收存 —— 这在当时,似乎为土地权属画上了句点。
但故事并未结束。2007 年,作为抚顺市政府派出机构的新抚顺棚厦区改造指挥部(负责人王立宽),突然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由,将兴顺公司及前法定代表人韩阳福告上法庭,要求终止合同、收回市政管理处那块 1459.4 平方米土地的发包权,并要求韩阳福移交相关证件。起初,两级法院均支持了指挥部的诉求。
转折出现在 2008 年 9 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二审判决,指令抚顺中院再审,这场权属之争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400 万借款与土地抵顶:一场待解的争议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场诉讼浮出水面。2008 年,殷延利以指挥部欠其 400 万元到期借款为由起诉,东洲区法院独任审判员陈福军主持调解,最终作出民事调解书:指挥部以二十五方块东北角的土地及房屋抵顶欠款。随后,抚顺市土地储备中心以 395 万元收储该地块,据称 2012 年前已将补偿款支付给殷延利。
但这场 "以地抵债" 的背后,疑点重重。
指挥部称通过补偿取得土地权属,却拿不出拆迁补偿协议、付款凭证等关键证据;三级法院已认定日新公司与市政管理处的拆迁协议合法有效,且兴顺、日新公司早已完成补偿,指挥部 "重复补偿" 的说法难以成立。指挥部又以持有土地证件复印件、1995 年 9 号文件为由主张权属,但文件并未涉及权属归属,且证件原件本应由日新公司合法持有。
更关键的是,指挥部向殷延利借款400 万元,始终缺乏银行收付款凭证、银行流水、财务账证等证据支撑。有人质疑:这是否是一场 "凭空获地" 的操作?
作为政府派出机构,指挥部行使公权力,王立宽的相关行为属职务行为。这场纠纷,究竟是普通民事争议,还是隐藏着更深层的问题?法官在审理中是否充分核查土地权属、厘清案件性质?这些疑问,让新抚顺的棚改故事,多了一层待解的迷雾。
城市更新中的反思
从千金寨到新抚顺,从棚户区到改造新区,这片土地的变迁,是中国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棚改本是为了让居民告别简陋住房,拥抱新生活,但当利益纠葛、权属争议掺杂其中,便考验着每一个参与者的初心与底线。
如今,新抚顺的高楼或许早已拔地而起,但那段关于土地、合同与公平的争议,仍在提醒我们:城市的进步,不仅需要钢筋水泥的堆砌,更需要清晰的规则、透明的程序,以及对每一份权益的尊重。毕竟,每一座新城的崛起,都应站在公正与法治的基石之上。
举报/反馈
发布于:湖北省启牛配资-炒股配资股票-证券配资炒股开户网站-专业股票配资资讯网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